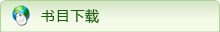|
乌托邦思想的历史谱系及当代价值 |
|
2011年09月21日 |
|
乌托邦思想的历史谱系及当代价值
——评张彭松《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
靳凤林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北京 100091)
“乌托邦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给定的现实社会,并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总体性构想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又由于乌托邦观念是强调对人类的理想社会总体性建构或设想,而不是通过现实社会的某一种要素或同一性机制,如技术、理性来实现,故可以称之为‘社会乌托邦’。”这是张彭松的《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以下简称《乌托邦》)一书对“乌托邦”概念所做的基本界定。以此认识为出发点,作者认为,迄今为止,人类对待社会乌托邦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将其作为照亮人类未来的希望灯塔,为人类历史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二是把乌托邦看作是一种对未来希望的诅咒,反对把人类历史过程当作一种神性设计来看待。综观全书内容,作者在是书中更多的是站在前一种立场上,强调乌托邦精神之于现代人类的积极意义。究竟如何看待乌托邦现象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笔者试图依据《乌托邦》一书提供给我们的基本思路,对之做出以下诠释和评议。
一、反思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历史谱系
作者在是书第一章中,首先对西方社会乌托邦理论的思想成因、本质特征及其价值意义进行了深度剖析。我们知道,学界对某种社会思潮进行分析时,通常从该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出发,进而叙及其主要理论内容。与之不同的是,张彭松在是书中更多的是从西方社会的内在思想特质出发,着眼于西方思想史的理论谱系来展开乌托邦理论的探讨。他认为,乌托邦理论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思想史上不断地花样翻新,其重要的理论前提:一是西方社会“本质先于存在”的悠久思想传统。作者追溯了自古希腊赫拉克里特至近现代黑格尔的思想历程,认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张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背后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世界,本体世界是现象世界变化的动因、源泉和终极归属,后者优于和高于前者。二是西方社会“国家优于个人”的价值观念。作者主要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例,深入说明了古希腊社会为避免城邦的瓦解,大力排除个人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而这一思想传统又在近现代卢梭的“社会公意”和黑格尔的“国家观念”中得到进一步的回应。正是在上述两种思想的共同作用下,使得西方社会的乌托邦理论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三大特征: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张力结构、本真性乌托邦的不在场、乌托邦观念由空间到时间的转换。作者认为,乌托邦作为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终极价值追求,一方面,它构成了西方社会自我更新、自我反思的内在思想动力;另一方面,它一旦转化为具体的乌托邦运动和实践,又极易导致专制主义和独裁统治的出现,特别是对乌托邦“在场化”何以必然导致这种不良社会后果所做的分析,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所赋予作者的睿智性和机警性。
作者对乌托邦理论所做的上述分析,无疑为人们深入把握西方乌托邦理论的思想成因、主要特征和价值意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系。当然,每位学者的知识背景不同,致思手法和笔调意趣各异,对西方乌托邦理论所做的探讨必定会呈现出自身的理解和解释特征,其他学者可以依据各自的理论图式对乌托邦现象做出不同的规定和区分。笔者认为,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看,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一方面表现在肉体器官进化的差别上,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智力和思维的进化使人类成为在历史中生成的、向着未来敞开着的和不断建构中的未完成的存在,从而表现出一种自我超越的独特本性,正是人类的这种生活于“实然”状态中,不断探求事物间的“必然”,力求达到“应然”的类本质特点,使之对社会乌托邦的向往永远无法释怀。对此,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曾经借助对感性、知性、理性各自特点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深入说明了人类何以对形而上的乌托邦本体世界永远无法放弃的问题,如果我们沿着康德的思路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也许会像张彭松一样,开辟出另一条崭新的乌托邦理论探究之路。
二、重新思考马克思对乌托邦理论的批判和超越
作者在是书第二章特别申明:“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乌托邦,而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为证明这一观点,作者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轨迹的探索,深入阐述了由马克思所完成的从思辨哲学向实践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作者认为,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既避免了漠视现实生活的过分理想化的乌托邦主义思维,又摆脱了对现实生活缺乏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庸俗唯物主义,确立了以物质生产为基本要素的实践本体论哲学,从而真正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价值与真理的内在的、动态的总体性统一。作者指出,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都发生了多种变化,但由于实践本体论内含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在统一,使之能够有效应对各种挑战,作者分别以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两种当代哲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批评为例,论证了只有坚持实践本体论的观点,才能有效克服上述两种哲学流派的思想弊端,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弗兰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提出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剖析。丹尼尔·贝尔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二战之后,经过全面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改革,其社会的阶级构成、人们的职业分工、日常的生活方式、国民的文化心理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方国家已经完全接受了混合经济体系、全民福利社会、政治权力制衡、多元价值观念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模式,这就使得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社会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论为代表的激进性意识形态彻底丧失了以往的感召力,由之,以意识形态来区分和彰显社会本质特征的时代已经走向了终结。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发表于冷战后期的1960年,20多年后,伴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预言。此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1992年)中,带着极其乐观的情绪大声宣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战胜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社会统治的最后形态,历史就此走向了最后的终结。
针对上述主张,作者在对历史终结论的思想实质、理论来源进行深入分析后,再次强调指出,本然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虽然凝结着传统乌托邦理论有关道德信念和终极关怀的成分,但他建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并以人们现实的实践活动为前提,故与丹尼尔·贝尔和弗兰西斯·福山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理论存在本质区别,应该说张彭松仍然是在遵循学术界“回到马克思”的思想理路来对“共产主义并非乌托邦”这一命题展开论证的。但在笔者看来,丹尼尔·贝尔和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针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现实弊端和最终失败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特殊现象所做的总结,要真正驳倒他们的理论主张,除了遵循“回到马克思”原典思想的理路外,还需要从马克思的原典思想中跳出来,对马克思本人的共产主义理论与苏联版本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和本质差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面更新、当今时代如何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世界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具体路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深层次说明,当然,这一任务决非张彭松的一本《乌托邦》所能完成,它将是摆在我国思想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长期性历史任务。
三、乌托邦理论之于现代人类的是与非
作者是书的重点是讨论乌托邦与现代性的关系,故用了两章(第三、四章)的篇幅探究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和超越现代性的路径选择问题。作者认为,“现代性是指在后传统的西方社会中建立起来,并在20世纪开始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或发展模式。”其典型特征是工具理性至上和个人主义盛行,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模式,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同质化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文化领域表现为世俗化的大众娱乐方式。现代性既斩断了与过去一切传统的联系,又杜绝了和未来完美理想的沟通,只是将瞬间的“现代”永恒化和绝对化,反映在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上,就是彻底放弃对神圣与崇高事物的形上追求,只关注世俗器物层面的形下享受。现代性在给人类生活提供极大方便和舒适的同时,也将人类拖入一种巨大的风险旋涡中而无法自拔,要祛除现代性自身的附魅,避免人类文明的毁灭,重建人类乌托邦观念,无疑是人类超越现代性的理想路径之一。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张彭松在是书的最后部分强调,“社会理想”与“社会乌托邦”之于当代人类各自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价值。他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和当代中国具体国情认识基础之上的社会理想,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它本质上不同于完美无缺的乌托邦幻想。然而,这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乌托邦思想仅是政治思想史上不甚重要的孤曲,是一种古老社会理想的垂死呻吟,进而彻底否定乌托邦之于当代人类的重要价值。因为乌托邦作为人类对社会统一性、总体性、和谐性的追寻,其根本性作用在于:一方面,它蕴涵着强烈的批判精神,能够和现实保持一定的思想距离,帮助人类看到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另一方面,任何一种乌托邦尽管永远无法还原为现实要素,但它能够帮助人类建构起一种终极性的价值制衡和道德制约机制。恰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人的成熟并不表示人今后不再做梦,而是知道哪些是梦,哪些是现实,正是有了这个梦,人才充满了无尽的希望和期待!”
应该说,张彭松的以上论述充分展示了乌托邦之于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但是在笔者看来,要全面揭橥乌托邦之于当代社会的正当性本义,还需要从人类终极层面的生死伦理中阐幽发微,做出提纲切义的解释。正如笔者在自己的《死,而后生——死亡现象学视阈中的生存伦理》一书中曾经指出的那样:“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却又要面对一个无限的宇宙;人的活动是局部的,却又要受到一种整体的关联;人的存在是相对的,却又感触到时空本身之绝对的存在;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却领悟到一种超越生命的永恒意义。面对这种有限对无限,局部对整体,相对对绝对,短暂对永恒,特别是面对自身死亡必然性的客观现实,人的心灵世界时常会受到一种剧烈的震撼,恐惧与绝望就是这种情感颤动的具体表现。然而人类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它不是消极被动地应对这一现实,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去创建某种死亡形上学来抚慰自己战栗的心灵与情感,由此我们说死亡形上学的内在可能性和必然性从根本上是由于此在对自身有限性的更本源的阐发和更有效的把握而被建立起的。”依据这一思路,笔者认为,从根本意义上讲,乌托邦之于人类的正当性根植于人类永远无法克服的生死冲突之中,只要人类存在着生与死的对抗与冲突,就永远不会放弃对最初“伊甸园”的回忆和对最终“幸福天堂”的追求,这种回忆与追求不会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生产力的无限发达和人类物质财富的剧增而最终消失,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众多杰出科学家皆是基督徒,为什么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奥姆真理教”和“法轮功”之类邪教组织所宣传的“精神乌托邦”还能找到存在的空间。
笔者最近陆续阅读了万俊人先生主编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包括张彭松是著在内的这套汇聚中外政治思想精华的“政治哲学丛书”,深切地感受到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历次改革中屡屡被推迟的最为棘手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然成为制约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中国在21世纪的基本走向,甚至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世纪初前30年我们对这一问题所做的思考、选择和作为。而这套丛书正是站在这一理论制高点上,从社会政治发展的终极层面回答了什么是政治哲学、我国当今社会为什么需要政治哲学、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哲学这三大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相信随着这套丛书的陆续面世,广大读者会从中外政治哲学的交融碰撞中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和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的未来走向做出自己的判断,进而寻觅到自己心中的理想答案。
作者简介:靳凤林,男,1963年生于河北省新乐市,哲学博士,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政治伦理和生死伦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