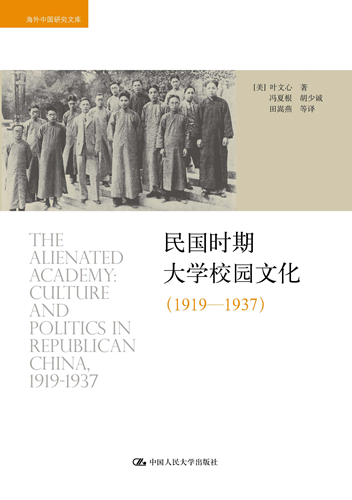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作者:叶文心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定价:62.00元
美国华裔学者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是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其他相关的较好的大学史著作还有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等),这本初版于1990年的著作,即使放置在今天的学术视野来看,也丝毫没有过时之感。
这些年,对民国大学的怀旧成为文化界的一股经久不衰的热潮,何兆武《上学记》、鹿桥《未央歌》、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等口述史、文艺小说与回忆录作品,让很多如今在日益工具理性化和行政化的宰制之下疲于奔命的师生,都对那段消逝的民国大学史有着重温进而接续的心情,与此相对照的是,却是当代中国大学史写作的整体性缺席,即使偶尔有一鳞半爪的大学史,也多是索然乏味的大学编年史,简单地罗列大学历史沿革、规章制度、师生人数等,根本无法有力地将大学的精气神及其在历史中的挑战与困境叙述出来。因此,这些大学史既无法建构出该校自身的历史文化脉络和学术传统,也没能将大学放置在政经框架和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进行细致分析,这样的大学史的命运自然是自产自销而无人问津的,说到底不过是大学的一个自娱自乐的形象工程罢了。
我不得不说,这绝非一本可读可不读的校园文化的“软书”,而是一本将民国时期三种类型的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等)归置在学术、社会与政治的三角互动之框架中进行考察的文化史著作,因此可以说中文版的书名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叶文心治史的长处(包括《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在于整体感强,有着历史的通透和洞见,注重细腻之处的深描,而且她的史学语言也是格外清新和优美,不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滥用学术名词。因此,这可以说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著作。
大学与社会革命
此前很多著作都比较关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但对于民国大学格局中至少占据三足鼎立之一的教会大学缺乏必要的关注,其实当时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学术与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叶文心的著作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圣约翰大学的成立初衷、团队精神、校园社群和文化、及其面临的民族主义挑战。
根据作者在此书以及《上海繁华》一书中的考察,当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私立大学,是上海的资产阶级阶层再生产的最重要的管道,而且依托于上海这个最具有国际性和现代感的大都会,这些大学成功地实现了儒家中国的知识范式的现代转型,通过科学知识、职业技能、良好语言等来获取财富,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职业伦理,但是这种对于财富的渴求与追逐,并未导致暴发户式的浅薄与庸俗,因为这些教会大学有着良好的道德训育与宗教熏陶,这就类似于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
但是,即便如此,在当时那样一种强劲的民族主义潮流之下,作为天然具有保守性质的教会大学,自然会面临来自社会各界(自政府到知识阶层乃至普通民众)的指责,当整个国家都在民族危机之下摇摇欲坠,一个私立教会大学的大学生却还在做着成为高等华人的美梦,这既在道德上是不可欲的,也是在现实上不可能的。
更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叶文心在著作中对上海大学的分析。上海大学如何从一所被时人所不齿的“野鸡大学”成长为一所“革命大学”,这在此前的历史叙述中是面目模糊的。在于右任担任校长后,左翼知识分子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彭述之、李季、李达等人都成为上海大学的教师,当时上海大学最著名的社会学系开设了诸如“近代中国外交史”、“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史”等课程,而这些课程为年轻一代的学生灌输了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马列主义观念。
读者切莫以为这仅仅是革命大学上海大学的独特现象。事实上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上海的左翼文化蓬勃兴起,唯物辩证法等理论著作风行景从,年轻一代的左翼在政经结构上边缘化,反而强化了其心态上的激进化和控制文化话语权的冲动。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早期成为出版社会科学读物特别狂热的时期,社会问题与社会科学成为上海大学校园文化的两个关键词,个人问题在革命理论的映照下,就不再仅仅是个人或家庭可以解困的,而成为具有共通性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大量引入社会科学理论,因此,当时翻译出版的最大宗就是社会科学理论,理论成为照亮灰色生活的最大探照灯,也是指引年轻人走出人生困境的明灯。
而上海大学可以说是这一现象的风暴中心,正如叶文心所言,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上海大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据点,这些知识分子领导并启发了整整一代进步青年。如果说一所大学体现了那些支持它的人的集体热情和信念,那么上海大学就是一所为推翻通商口岸体系、掀起社会革命而建的大学。
高等教育与社会平等
自然,即使对处于历史风云激荡中的民国大学来说,除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革命文化的传播,或者资产阶级文化的塑造,同样存在着大学生如何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这部分内容(书中第六章《大学生活之代价》)在我看来很有价值,因为之前的民国大学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写作更多的是关注政治和文化的层面,而相对轻忽了日常生活的层面。正如革命有神圣与世俗的双重性格一样,大学同样如此。
大学既是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又是高度政治化的空间,同时还必须应对贫困与苦难。叶文心通过大量的当事人的记录和事后追忆,呈现了民国大学的收费、学生日常生活等多重层面。显然,私立大学的逐利冲动压制了很多年轻人的求学欲望,而公立大学的制度性保障,却也培养了年轻人志怀高远超越世俗的情怀。作者呈现了社会舆论、政府、知识界等对当时学生群体的各种评价,高等教育成了社会公平最重要的聚焦点。
亦学亦官的陶希圣就曾经尖锐地批评上世纪30年代的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级小学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更就能够升大学的来说,大抵是中资以上的富裕人家。大学则是所谓‘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
或许正因如此,上海一些昂贵的私立大学里的学生,在教育部的报告里呈现出的完全是消费主义者的形象:“这些大学生们从不关心任何严肃的事情。他们过着娱乐休闲的生活。他们的衣着昂贵,饮食考究。他们消费进口商品。他们经常出入影院和舞厅。他们出门坐着雪佛兰汽车。他们既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关心他们的学业。”高等教育成了社会结构再生产的有效机制,而堵塞了社会不同阶层流动的可能性,这自然就会引发底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强烈的不满,而这些学生的公共形象,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民族国家处境中更是显得格外刺眼。
叶文心敏锐地注意到了当时的社会舆论的表达困境:“当舆论聚焦在大学生的失业问题上时,大学毕业生被看作清寒子弟,需要工作来养家活口。但是当舆论聚焦在教育机会的结构性不公时,大学生又被描绘成资产阶级的富家子弟。”这充分说明了当时大学生群体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以及舆论在议论大学生群体时的复杂心态。
无论是培养资产阶级的圣约翰大学的分崩离析,还是培养左翼激进者的上海大学的被关闭,都在映照一个急剧变动的大时代里学术、文化与政治之间强烈的依附性与疏离感,近代中国大学的主体性仍旧在艰难地重建,它必须面对民族主义话语的挤压、政治力量的控制、社会舆论的话语暴力,不同的大学与政治、资本力量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在这种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大学呈现出的“整体情绪氛围明显陡然消沉”,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的政治幻灭感成为一种尖锐的集体心态。当稳定成为大学校园压倒一切的政治诉求的时候,其实,它也悄悄地酝酿着反叛的潜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如此现代和西化的民国上海,左翼政治和左翼文化一直是它挥之不去的文化精神的内核之一。
□唐小兵(大学教授)

